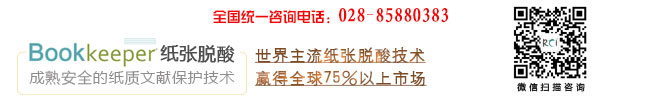《藏书报》古籍保护,保护什么?传承什么?
时间:2020-04-22 14:32:10来源:《藏书报》
文章来源:《藏书报》2019年第49期
作者:刘家真(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古籍的存藏永远是以用为目的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古籍藏与用的矛盾得以缓解。今天的科学技术使得古籍原件的信息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为用户所获取,但无论是缩微胶片还是数字化数据,其保存的便利性、保藏的条件以及可能保存的时间都是无法与纸张相比拟的。为避免历史的记录由于技术进步而丢失或无法完整地保留,古籍原件的长期保存永远是第一位的。
要满足广大读者感知古籍的温度、与古人跨时空握手的愿望,最好的办法便是高仿一些利用率较高的古籍,让它们以原件的化身来满足读者的需求,而不能感情用事地将古籍原件任普通读者触摸。可以接触古籍原件的人,一定是由于研究或工作需要必须见其真容者,如版本鉴定、涉及古代制作工艺的特别研究以及数字化工作者等。
在保护古籍的方法上,无论是保藏还是修复,目前我们更多的是经验主义的做法,即对感性经验所进行的概括总结。经验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它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但仅是认识的开端,它需要运用科学的思维、开放和发展的视野对其检验、深化,使其上升到科学理论的层面,才可能使这些经验成为指导普遍实践的理论,而不至拘泥于狭隘的个人经验或“相传”、拘守“成规死法”。今天我们要在古籍保护的基础理论上多下功夫,特别是在古籍保护技术的基础理论上,使我们保护古籍的方法科学化。古书上记载的很多保护方法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要发掘出其中的科学原理以推陈出新。在修复技术上,这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为什么一个师傅一个法,为什么很多古书上记载的不少有效的清洗方法今天都失传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教授给下一代的是个人的经验而不是科学知识。

今天,我国古籍保护方面的研究院已有了三个,三个研究院各有特色,在古籍保护的基础理论上应该分工合作,而不要顾及大而全。例如,中山大学在西文修复上很有特色,天津师范大学在古籍整理与鉴定上独树一帜,而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的众多理科学者,更利于从理化生的角度探索古籍保护技术的基础理论,包括古籍材料学、古籍载体的病理学,以及抢救、维护古籍的基础理论等。三个研究院还可以集合科研力量来解决与保护古籍相关的、需要横向研究才能解决的科学问题。由此可见,我国古籍保护基础理论研究的平台已经搭建,关键就是如何深入研究的问题了。

有关古籍保护的科学研究一定要脚踏实地,也就是要在科研工作团队中汇集具有实践经验的古籍保护工作者,理论联系实际地进行相关研究,否则就会将理论研究推向空谈或缺乏落地的基础,古籍保护的基础理论成果将会被社会束之高阁,变为空谈。这点是必须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因为国内高校的教师多为直接从高校走向讲坛,缺乏实际工作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