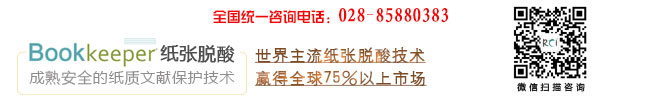敦煌遗书脆化成“酥皮点心”,还能修好吗?
埋首于微弱、泛黄的故纸堆中,在灯下如外科医生般细致地对古书进行着揭、拆、压、包、订……静水流深、皓首讷言,大概是许多人对古籍修复师的想象吧。
供职于国家图书馆,“从医”三十六年、修复过敦煌遗书、西夏文献、《永乐大典》、天禄琳琅等等众多珍宝级古籍的朱振彬,沉静,却不是想象中的白头老先生。
把“砖头”蒸软
1983年春,朱振彬出师回到国图善本组报到,正式成为一名古籍修复师,开始接触真正的善本。
那时候,朱振彬的工作间就在北海公园隔壁的国家图书馆旧址。优美的外部环境,与朱振彬桌案上的一番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工作没多久接手修复的一批彝文书,由于曾经的保存条件不好,书上沾了不少动物的排泄物,时值盛夏,刚一打开书卷,骚臭味儿就扑面而来。明代《阙里志》纸张已经絮化,一打开书卷就往外飞毛毛,恰逢天气炎热没戴口罩,朱振彬和几位同事全都中招,不停打喷嚏,还长了一脸红疙瘩。
虫蛀、鼠啮、火烬、脆化、酸化、粘连、絮化……古籍所患的疑难杂症,每一种都不好对付。修复一叶纸常常需要一两天,遇到疑难杂症多的书叶,一叶甚至需要十天半个月才可以完成。

就拿出现频率较高的病症“粘连”来说,对付的办法就是——揭。也就是把经年累月受到水渍粘连在一起的书叶与书叶分开。古籍粘连程度不同,可以采用干揭、湿揭、蒸揭等不同的手法。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一次古籍修复展上,曾经展出过这样一些古籍——曾被水浸泡严重,又经过漫长的岁月,书叶已经粘连、硬结成砖头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就只能像蒸馒头一样用蒸锅蒸古籍,让纸张间的粘连部分慢慢化开。
师傅那一辈还用竹屉蒸,到了朱振彬这一辈已经改成不锈钢锅。蒸揭技术的核心,就是火候的把握。把古籍外面包上旧纸、裹上毛巾,而火候的掌握全靠经验,蒸得时间长了,蒸汽冲击书叶会对古籍的纤维造成破坏;蒸得短了,又起不到作用。宋朝大文豪苏轼的表哥文同,曾著有《丹渊集》。国图所藏明版《丹渊集》就是板结较严重的古籍,需要蒸揭。每一册大约需要上锅蒸三至五分钟。时间一到就得赶紧取出来,剥开包裹的毛巾和旧纸,用起子两毫米、两毫米地将纸张与纸张分开。力道重了纸张会被磨破,下手慢了又会错过热乎气儿,让分离难度加大。快与慢,轻与重,就都在毫厘之间,都在朱振彬的手里。

天禄琳琅专藏之明版《丹渊集》修复前

天禄琳琅专藏之明版《丹渊集》修复后
大战“酥皮点心”
而所有病症的治疗中,絮化、脆化也是难症。但凡得了这两种病,古籍的书叶就像“酥皮点心”一样,摸不得碰不得。
198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大型古籍修复工程——敦煌遗书修复正式启动。1991年,修复工作真正开始。那时候,国家图书馆的老一辈修复专家均已退休,朱振彬和四五个年轻同事就成为修复主力,大战“酥皮点心”。
敦煌遗书是对1900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17号洞窟中一批书籍的总称,包含了公元2世纪至14世纪的古写本及印本,总数约五万卷。它如今散落在世界各地,其中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内的万余卷是镇馆四大宝之一。由于藏量巨大、年代久远,敦煌遗书的修复只能以抢救为主,重点修复那些“病入膏肓”的书卷。书卷因纸张不同,破损也呈不同状态。这其中,纸张采用竹纸的古籍,常常会脆化为很多细小的碎片,有的寸许,有的也就大米粒儿一般。这时候的朱振彬俨然是拼图能手,把古籍拆开,小心翼翼揭开每一叶,兜住它的碎片,再耐着性子,付出几倍于普通修复的时间,把这些碎片拼正确。

敦煌遗书专藏之《成唯识论了义灯钞科文》修复前

敦煌遗书专藏之《成唯识论了义灯钞科文》修复后
拼好之后,要用毛笔和特制的糨糊进行“微相入”。朱振彬所使用的“微相入”方法,早在北魏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书有毁裂,郦方纸而补者,率皆挛拳,瘢疮硬厚。瘢疮于书有损。裂薄纸如薤叶,以补织,微相入,殆无际会,自非向明,举之,略不觉补。”也就是说,书有了损坏,出现了裂口、裂缝,把纸简单地剪成方块去补书,书叶一般都会出现蜷缩现象。补过的地方形成瘢疮状,又厚又硬。这样的补丁对于书是有损害的。撕些像韭菜叶一样薄的纸用来补书,只使书叶破口边缘和补纸边缘微搭上一点,近似于没有什么搭界一样,如果不是向着光亮把书拿起来看,大致是看不出补过的。
每每到这一步,朱振彬的工作间里都安静得仿佛时间静止。他浑身肌肉高度紧张,拿起充当“手术刀”的普通毛笔,蘸上比米汤还稀的糨子,待笔尖不滴糨子时,才轻轻点在碎纸片的边缘,牵引着碎片和书叶之间的毛茬轻轻搭上。这时候,下笔稍微重一点,碎片就粘在毛笔尖上不肯下来,再一提笔,干脆就彻底被从古籍上揭走,损伤书籍。下笔轻了,碎片和书叶之间搭不上,一拎起来碎片掉了,又得重拼。
还有些古籍采用的是皮纸,皮纸的纤维略长于竹纸,老化时形成的“酥皮”并不会断裂成一个个碎片,而是纸张的纤维异常稀疏,絮化得就像豆包布,叶面上的字迹也都走样变形。给这样的书叶做“微相入”时,每一次操作的空间还不足一毫米。“致力于毫芒微渺间,真有临渊履冰之危,稍有不慎就将对书籍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朱振彬说,此时成败的关键就是经验。

敦煌遗书专藏之《成唯识论了义灯钞科文》修复前

敦煌遗书专藏之《成唯识论了义灯钞科文》修复后
“古籍重装如病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则随剂而毙。”朱振彬心里一直有个底线,凡是自己没有十足把握时绝不下手修复。为保万全,他变得越来越要求完美,越来越注重细节,这渐渐改变了他的性格,让他越来越沉浸在自己与书的世界中,更加沉默。
技术传承易 原料再觅难
现在,朱振彬像自己的师傅一样,开始带徒授业。
2006年,国家图书馆举办“文明的守望——国家图书馆古籍珍品选大型展览”时,朱振彬和同事们曾经统计过,当时全国的古籍修复人才不足一百人。古籍修复师,是一群比大熊猫还要稀少珍贵的人。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国启动了古籍修复人才的培养。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开办古籍修复培训班,培训业内人士,技艺高超的修复师们采取一对一的形式,带徒授业;中山大学和复旦大学还开设了古籍修复的硕士研究生教育……在国图善本组,修复师史无前例达到了十九人。
眼看着技术的传承步入正轨,朱振彬心里却在担心另一件事——古籍修复所必需的传统原材料越来越少。
就拿朱振彬2014年起正式开始修复的清代皇家内府天禄琳琅藏书来说。这是清代宫廷所藏宋、元、明、清珍籍的精华,是中国古籍的奇珍。这批古籍异常精美,函套以纯真丝装饰,每一册书卷上都钤有“乾隆御览之宝”“五福五代堂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等大印。而且古籍中的一部分纸张采用了中国古代造纸术巅峰之作——开化纸和太史连纸。可如今,这两种纸的造纸术已失传近百年。国图也是靠百余年积累才留下少许。在朱振彬的桌案上摆着很多个材料袋,每一个材料袋里都是些零零散散各种颜色的小纸条、小纸片儿,每次拿出一种使用,朱振彬也都格外小心,每次用完剩下的一点儿也都舍不得扔,仍旧放回材料袋里,以备不时之需。
朱振彬曾听师傅说过,从前老先生们都有一大雅兴,去琉璃厂寻觅古纸,这既带有一定的文化自觉,又受修复理念驱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老先生们还能收到零星的开化纸及太史连纸,但后来市面上几乎不见踪影。现在大多数业内人士,对这种顶级纸张也只是闻过其名,从未见过其貌。

修复材料的危机,一直困扰着修复师们。2003年,国图启动西夏文献修复工程。这批经折装古籍所用的是麻纸和皮纸,可如今已再无麻纸,只能尽量找纤维的长短、纹路以及纸张薄厚相近的纸张来修复。即便是皮纸,要想找到满意的也不容易了。前几年,朱振彬和同事们经多方寻访才从贵州进了一批枸皮纸。“经过鉴定,确认这些纸是售卖者的爷爷以古法手工造纸抄出来的,这样我们才敢买。”
遇到实在没有合适的旧纸,就只能用新纸了。朱振彬说,在新纸选用上也得力求选与原书纸质、帘纹、薄厚相一致的手工纸。在使用此类新纸之前,还要对其酸碱度、拉力等进行测试。目的就是使用时不能对原书造成伤害。即便通过这许多测试,新纸仍然存要面临一个大考验——染色。新纸必须染成与古籍纸张色泽相仿,具备古意,才可以使用。这样的染色工作,2014年起修复天禄琳琅藏书的过程中,已经开始了。
国图古籍修复的工作间里,有一个如中药房药柜一般的大柜子。每一格抽屉里,分别放着橡碗子、茶叶、黄柏、栀子、姜黄等染色所需的植物。到底选什么植物来染色,这并不全由朱振彬说了算,而是要遵从古法。为纸张染色,历史悠久。晋唐时期的敦煌写经用纸就大量采用了黄柏汁染色,史称“潢纸”。明代高濂在其所著的《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中也提到了运用橡碗子、黄柏等染配黄色纸张。 “黄柏一片,捶碎,用水四升,浸一伏时,煎熬至二升止听用。橡斗子一升,如上法,煎水听用………” 修复天禄琳琅藏书时,朱振彬在清《武英殿刻书作定例》 中也找到了清宫刻书作为染色而采买颜色的一份采购清单。其中就包括了橡碗子、栀子、藤黄等植物。“这些资料都证明,用橡碗子、栀子、藤黄等植物染纸自古就有,其悠久的历史印证了此法的安全。用这些植物柒过的纸用于天禄琳琅藏书的修复,对珍籍不会产生有害的影响。”
为了确保修复材料不含化学物质、不含酸,朱振彬连糨糊也不敢在市面上买现成的,而是带着徒弟们自己动手制作。他们将买来的纯天然小麦面粉和水去除面筋,再把粉子洗出来晾干,这样才能得出纯天然的糨糊原料。在修复过程中,为了节省时间,朱振彬曾经带着徒弟们尝试使用分离设备来提取小麦淀粉。可试过几次之后发现,这样提取出来的淀粉冲成糨糊之后,呈现凉粉状态,太过透明。而且糨糊被冲熟之后也闻不到麦香的味道,再用手搓一搓,没劲。师徒几人反复琢磨分析发现,问题还是出在分离过程。之前用纯手工分离浆水时,浆中多少带有一些筋,这样制做出来的糨糊补书后,书叶平整而不失浆糊的劲道。而采用机器分离,在分离过程中太过强调纯度了,这样提取的小麦淀粉补书后其牢固程度就降低了。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再提取淀粉时格外注意,才使得糨糊的黏度大大提高。
糨糊制成,待到修复古籍时,调糨糊所用的水都得是纯净水或蒸馏水。“只有这样的糨糊才能真正做到可逆性,如果日后修复技术进步了,可以把我们现在的修补以水洗掉,重新再来。”他要操心的已不止手法那么简单,古书好像婴儿一般,牵挂着他的全部身心去照顾。

朱振彬修复工作照 | 方非 摄
如今,采用古法手段仿制古籍修复材料的尝试已经开始。全社会对古籍保护的重视正吸引越来越多社会资源投入其中。朱振彬三十六年“书医”路,也从几乎无人同行的惨淡,迎来了现在广受关注的灿烂。可他依旧沉默着,最感兴趣的话题永远是手中的古籍。敦煌遗书、西夏文献、《永乐大典》、天禄琳琅……他的修复故事还在继续。
(本文节选自《国宝修复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