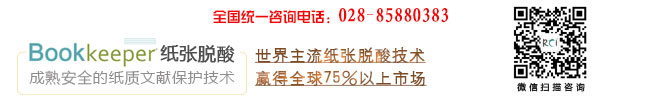黄显功 | 如何开创古籍保护新时代
时间:2020-01-10 09:55:24来源:藏书报
文 | 黄显功

黄显功(上海图书馆)
现在,古籍保护工作采用的都是传统的方式,普查也好,编目也好,特别是近几年来所进行的古籍修复工作,仍然是以传统的修复方式为主,人才培养方式也是师带徒的传统路数。现在复旦大学按照文物保护创新研究的思路,引进现代的科学管理的方法,运用现代的一些科学技术,以多学科的综合手段来开展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我认为这促进中国古籍保护工作进入了新阶段,使我们古籍保护工作得到真正的实质性的提高。而对于从事古籍工作的人来说,提高“以科技为指导”的这种保护意识,尤为重要。
我们看到意大利对古籍修复人才的培养,目标不是培养“工匠”,而是培养“修复师”。“修复师”和“工匠”的概念完全不同,修复师的知识结构、所受的教育和训练都是具有高标准的。我们搞过很多古籍修复培训班,成果也很令人欣慰。目前,全国受过此类培训者可能超过1000人,那么这1000人中,有多少能称之为“修复师”的,我看仍需检视。还需要反思的是,在面向未来的新阶段,我们如何来开创文物保护的新时代?
从2007年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以来,十余年的古籍保护成果显著。全国不少地方完成了古籍普查,出版了不少登记目录等,这些都是很具体的成绩。但是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觉得还要有一个警觉:保护起来就可以了吗?古籍保护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我分享一下自己最近的一个小经历,我曾接到过两个电话,一位出版界朋友,一位高校教授,分别托我帮忙向某两个图书馆打招呼:想看某部古籍,目的是看能否影印出版和进行学术研究。但是去了之后图书馆不让看,原因都是该古籍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这就让我思考,古籍保护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保护起来就可以了吗?得到“妥善保护”之后就应该是得到“合理利用”。那么“合理利用”又涉及“怎么来利用”?最有效的办法,一个是数字化传播,一个是出版图书。我们知道,“数字化”和“出版”也是对古籍进行再生性保护的有效方法。
古籍保护的终极目的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果束之高阁,贴上一块名牌,表明这是珍贵古籍,不让大家使用,这恐怕与古籍保护的目标背道而驰了。我们许多同仁还没有觉察或者不愿意觉察这个认识误区,我觉得这是要呼吁的。
古籍存藏在一个地方,它的文物价值是不会改变的,而它的文献价值是通过传播来体现的,把它影印出版之后,并不意味着文物价值就降低了。现在我们有人还是把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混为一谈,这种观念在我们的图书馆界还是有市场的。所以,我希望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能够牵头,鼓励图书馆开放馆藏,推动古籍利用的便利与普及。目前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古籍数字平台倡导数字资源开放,现在已经公布了7.2万部,这是非常好的举措。
另外,应该加强馆际之间的合作出版,图书馆也应该加强和高校的合作。比如浙江省图书馆和浙江师范大学合作开展《两浙文丛》项目,这是非常好的合作范例。在图书馆从事古籍保护的同志,未必就对古籍的内容熟稔,对古籍文本的研究大部分都比较缺乏,但如果利用古籍资源和高校进行合作开发,那对古籍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来说,成果一定是显而易见的。
这十几年来古籍保护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希望古籍保护不要走另外一个极端:偏保护,轻利用。对于古籍的利用方式,要创新,需开放。我想作为图书馆人,作为中华古籍保护工作者,不仅把古籍守护好,还要把它利用好,传播好。